《我討厭韓國》爆火:韓國人又拍抹黑自己的電影? (Loading...)
資訊 三聯生活周刊 2023-10-02
正值青春年華的桂娜出生在韓國首爾,畢業於韓國首屈一指的藝術類院校弘益大學,畢業后在首爾一家金融公司工作,有一個感情穩定的男朋友。這履歷聽起來算得上一帆風順吧?但桂娜卻經常暗自琢磨:「還不如直接去死呢。」她時刻在心裡盤算著要離開韓國。
桂娜是小說《我討厭韓國》(又名《走出韓國》)的主人公,小說出版於2015年,由這本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於10月4日作為釜山電影節開幕片首映。消息一出,著實吸引了不少眼球。
一向擅長往祖國臉上「抹黑」的韓國影視圈,這次乾脆堂而皇之地將這種不滿打在片名上,並將在其官方電影節上隆重亮相。無論是韓國官方還是韓國民眾,對文藝作品的開放程度再次刷新了外界的認知。

《我討厭韓國》海報
小說的作者張康明是韓國人,記者出身,書中許多素材來自他對韓裔移民的採訪,其內容的真實性幾乎蓋過了藝術性,也有人稱其為報告文學。客觀來講,作為小說它有些乏善可陳,但作為一個話題,它切實擊中了許多人的心坎,一度成為韓國的暢銷書。許多韓國人心知肚明的社會問題,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。
小說開篇便出現一段桂娜的內心獨白:「你問我為什麼要離開韓國?簡單說就是『因為討厭韓國』,說長點就是『不想在韓國生活了』。」桂娜的內心充滿了挫敗感,覺得自己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,「就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。」她自比為非洲草原上的瞪羚,每次獅子一來,就成了落單的瞪羚,因為不想坐以待斃,只能拚命逃離韓國。

擊垮桂娜心理防線的,是生活中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,比如上下班的路程。「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2號線從阿峴站出發,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?如果經歷過,你就會切身體會到,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,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。」艱難的生活練就了桂娜吐槽時犀利的口才:「那些號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,應該在早晨上班高峰時間去搭乘地鐵2號線試試,來回坐幾次,就不會嚷嚷什麼出生率過低的屁話了。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掛在嘴邊的人,並不用坐地鐵。」
每天如此辛苦上班的桂娜,乾的卻不是什麼如意的工作。桂娜的公司經營綜合金融服務,她供職於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,如果有人要進行高額度結算,核准中心就會決定要不要給他結算。每當交易無法進行時,卡主就會打電話來投訴,應對這種電話很是痛苦。桂娜不喜歡這份工作,沒什麼技術含量,也不可能升職,薪酬還低。她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多,每天都想著離開。

桂娜雖然出生在首爾,但家裡條件並不好,用她的話說就是「沒有半點家底等著我去繼承」。男友家人嫌棄她的出身,令這段感情看不到未來。父親是大廈保安,家裡三個姐妹,姐姐在咖啡廳打工,妹妹無所事事。從小到大,她都是和姐姐、妹妹同住一個房間,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的獨立空間。有時候她寧願去上晚班,這樣白天就可以一個人在家睡家了。家裡房子很老,每年一到冬天,父親就用厚塑料布把窗戶封起來,但冷空氣還是會鑽進來。無論地暖開多大,房間都不暖和,凍得人直打哆嗦。
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桂娜強烈的危機意識,使她年紀輕輕就開始操心養老問題。她一度計劃50歲以後退休,去濟州島度過餘生,用一輩子的積蓄買一間舊公寓。理由是越晚退休越費錢,人上了年紀后,身體各部分都開始出現問題,要去醫院看病。「反正我已經想好了,最後肯定選擇自殺。我可不敢想象,自己一直活到90歲、100歲,到時候顫顫巍巍的,站都站不穩。」桂娜說。

從小到大身邊許多人的經歷,桂娜看在眼裡,越發不敢對生活抱有希望。小時候,阿峴市場很熱鬧,人們都說只要去那做幾年生意,都會變成有錢人。可是桂娜發現,這麼多年過去了,市場里賣甜甜圈的奶奶並沒有變有錢。於是她想,韓國雖然成了發達國家,首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「可有些地方、有些人,依然和原來一樣,沒有一點改善。我就這樣待在這裡,沒人能保證我的明天會比今天更好。」
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,桂娜漸漸意識到,自己的痛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,而是被一種牢不可破的系統支配著。很多年裡,她一直過得渾渾噩噩,直到聽到一首歌。那首歌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,由韓國歌手Turtle Man演唱的《Bingo》,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。歌詞其實充滿正能量:「我熱愛腳下的土地,從未想過移民。」但桂娜卻聽得有些生氣,「每個人都覺得活在這個國家很累,心裡暗暗盤算著移民,可是又不想承認,於是用這首歌來催眠自己。」可是話說回來,為什麼不可以移民呢?那一瞬間,桂娜腦子裡冒出這個念頭。很快,她決定不去濟州島了,而是移民去澳大利亞。

《我討厭韓國》的故事沒有太多跌宕起伏,小說情節完全談不上引人入勝。主人公出國前後的生活都平淡如水,無非是描述移民念頭的產生和執行,寫成新聞特稿都不夠特別。但正是這種「普通」讓她看起來異常真實,無論是她的困境,還是她的掙扎,都像極了一個生活中的普通人,沒有大起大落的驚心動魄,有的只是小刀割肉的悲涼與刺痛,很符合生活流作品的特點。
近年來,韓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,在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作品中有所體現。電影《寄生蟲》對韓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揭示掀起了廣泛的探討;《我的解放日誌》對城市打工族的疲憊進行了細膩呈現;韓劇《天空之城》對中產家庭的教育焦慮也有深入展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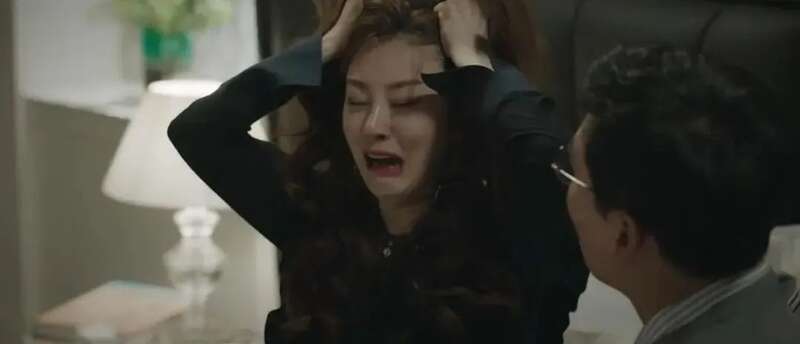
《天空之城》劇照
韓國文藝作品的敏感與其社會環境的高壓密不可分。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最新調查,2022年韓國資產上游20%家庭和下游20%家庭之間的差距創歷史新高,第一檔家庭的平均資產為16.5457億韓元(873.3萬元),相當於第五檔家庭平均資產2584萬韓元(13.6萬元)的64倍。殘酷社會競爭導致的教育內卷,在韓國也貫徹地相當徹底,學生能否考入SKY大學(首爾大學、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),直接決定了他們的未來,而這部分人只有2%。嚴峻的社會壓力直接反映到了生育率上,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《2022年世界人口狀況》顯示,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三年全球墊底,2022年這一數據為0.78。
結合這些社會現實去看《我討厭韓國》,會令人忘記它是本小說,其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內心的真實呈現,足以跨越情節和文筆勾起讀者的共鳴。作者經常會通過一些並不重要的情節來闡釋對事物的看法,對抒發觀點的重視甚至超過了塑造人物,可見其書寫動機多大程度上是由對議題的關注推動的。

在書中,作者經常借人物之口來諷刺韓國人。桂娜在澳洲交往的男友瑞奇是印度尼西亞人,他曾經在桂娜面前數落韓國留學生:「對韓國人來說,最上等的是澳洲人和西方人,之後是日本人和韓國人,再之後是中國人,最後是南亞人。可是在澳洲人和西方人眼裡,咱們全是東方人,他們根本分不清哪個國家是哪個國家。」當然,對韓國最狠的批判,還得交給「犀利姐」桂娜:「我的祖國只愛她自己,愛大韓民國本身,所以她只愛惜那些為她爭光的國民。比如金妍兒,比如三星電子。」
可以想象,改編成電影后,這本書里有多少觀點可以作為「金句」流傳,作為觀眾的「嘴替」讓人過把癮。不得不說,這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題材走捷徑的方式。比如作者在書中將幸福劃分為兩種,「資產式幸福」和「現金流式幸福」。前者是指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,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心裡,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供人支取,勤勞工作和攢錢買房就屬於此類。後者是指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,所以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的幸福,靠每個瞬間活著,桂娜想要的幸福便是此類。
對整個故事來說,桂娜出國后的生活到底有沒有變好?恐怕是讀者最關心的問題。小說通過一系列細節堆疊起桂娜的變化,其中許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感。

《寄生蟲》劇照
到了澳洲,桂娜報了一所語言學校學英語,為拿綠卡做準備,同時在餐廳打工。漂泊在異鄉的日子當然不容易,她租的房子由車庫改造而成,15平米大小,裡面只有書桌和床。因為英文很差,她只能做廚房雜工,連最低時薪都沒達到,只能拿8美元。但她依然一點點喜歡上了澳洲,也在對比中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更清晰的認知。澳洲地廣人稀,道路寬闊,陽光燦爛,與首爾的陰冷、擁擠截然不同。走在悉尼的街頭,亂穿馬路差點被車撞死,司機沒有罵她,而是一個勁兒地問她「還好嗎?」人們都很平和。她在澳洲結識的朋友,都活得瀟洒不羈,人生主要的任務是吃喝玩樂,而她在韓國的閨蜜們,則在十年如一日地抱怨工作和婆婆。
更重要的是,桂娜開始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自由的選擇。在澳洲,白領和藍領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不相上下,沒人爭著去坐辦公室,反倒認為干體力活也不錯。桂娜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同胞載仁便是如此,他一開始是為了學會計,後來發現對會計不感興趣,便改學了廚師。做廚師不需要碩士文憑,只需要在烹飪學校接受不少於900個小時的培訓,再實習一年,就有資格申請綠卡了。
當然,澳洲綠卡也有許多務實的好處,桂娜對此如數家珍。有了綠卡,就算不工作,也可以按月領失業保險金;得了大病,國家負責全部醫藥費;第一次買房,可以拿到2萬澳元左右的補貼;大學生子女每年能得到幾萬澳元的學費補助。

而另一方面,桂娜對韓國的恐懼並未消失,甚至進一步強化了。來到澳大利亞幾年後,桂娜聽到《Bingo》原唱歌手Turtle Man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。死之前他的生活已經很窘困,因為經營公司不善而債台高築,無錢支付高昂的醫藥費。與此同時,桂娜以前工作的金融公司也暴雷了,信用卡部門取消,一位員工自殺。桂娜想:「如果我依然留在韓國,能否抗拒這個命運的齒輪?恐怕不能。」
拿到澳大利亞綠卡后,桂娜曾經因為感情考慮回到韓國,最終還是放棄了。那次嘗試,讓她意識到,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與前男友志明短暫複合期間,桂娜回到韓國與他同居,同時嘗試找過工作,但找了幾輪都顆粒無收。想將注意力轉移到生活,也同樣無望。桂娜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貴,而是可以買到便宜的食材和酒水,住在溫暖有陽光的地方,身邊的人都愛笑,每月都能看看話劇、約約會。但這些男友都無法給她,他在電視台做記者,每天下班回到家已經是凌晨,經常忙到沒有休息日。一次,桂娜問志明:「你難道一輩子都要加夜班嗎?」志明回答:「所有人都這麼活著。」桂娜反駁道:「澳大利亞可不這樣。」於是,她決定第二次跟志明分手。

分手后,桂娜徹底決定待在澳洲,爭取拿到國籍。這次她的決心更堅定了,因為積極的念頭比消極的念頭有更強大的力量:「我這次去澳大利亞,不是因為討厭韓國,而是因為要變得更幸福。」
現實中,許多韓國人和桂娜一樣,選擇通過移民來改變命運。2016年,韓國媒體公布的一項移民調查顯示,78.6%的受訪者有移民傾向,移民理由靠前的幾位是:工作環境惡劣;收入不平等問題嚴重;對退休生活的不安。另一方面,許多年輕人正在逃離以首爾為主的大城市,選擇返鄉務農,韓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,2020年以來,有近50萬韓國人遷移到農場和農村地區,同比增長7%,其中二三十歲的青年佔一半。
種種人口流動跡象都表明,韓國人已對故土失去希望。現實主義作品的流行,不過是呼應當下人們最關心的話題。
桂娜是小說《我討厭韓國》(又名《走出韓國》)的主人公,小說出版於2015年,由這本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於10月4日作為釜山電影節開幕片首映。消息一出,著實吸引了不少眼球。
一向擅長往祖國臉上「抹黑」的韓國影視圈,這次乾脆堂而皇之地將這種不滿打在片名上,並將在其官方電影節上隆重亮相。無論是韓國官方還是韓國民眾,對文藝作品的開放程度再次刷新了外界的認知。

《我討厭韓國》海報
小說的作者張康明是韓國人,記者出身,書中許多素材來自他對韓裔移民的採訪,其內容的真實性幾乎蓋過了藝術性,也有人稱其為報告文學。客觀來講,作為小說它有些乏善可陳,但作為一個話題,它切實擊中了許多人的心坎,一度成為韓國的暢銷書。許多韓國人心知肚明的社會問題,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。
小說開篇便出現一段桂娜的內心獨白:「你問我為什麼要離開韓國?簡單說就是『因為討厭韓國』,說長點就是『不想在韓國生活了』。」桂娜的內心充滿了挫敗感,覺得自己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,「就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。」她自比為非洲草原上的瞪羚,每次獅子一來,就成了落單的瞪羚,因為不想坐以待斃,只能拚命逃離韓國。

擊垮桂娜心理防線的,是生活中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,比如上下班的路程。「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2號線從阿峴站出發,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?如果經歷過,你就會切身體會到,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,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。」艱難的生活練就了桂娜吐槽時犀利的口才:「那些號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,應該在早晨上班高峰時間去搭乘地鐵2號線試試,來回坐幾次,就不會嚷嚷什麼出生率過低的屁話了。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掛在嘴邊的人,並不用坐地鐵。」
每天如此辛苦上班的桂娜,乾的卻不是什麼如意的工作。桂娜的公司經營綜合金融服務,她供職於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,如果有人要進行高額度結算,核准中心就會決定要不要給他結算。每當交易無法進行時,卡主就會打電話來投訴,應對這種電話很是痛苦。桂娜不喜歡這份工作,沒什麼技術含量,也不可能升職,薪酬還低。她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多,每天都想著離開。

桂娜雖然出生在首爾,但家裡條件並不好,用她的話說就是「沒有半點家底等著我去繼承」。男友家人嫌棄她的出身,令這段感情看不到未來。父親是大廈保安,家裡三個姐妹,姐姐在咖啡廳打工,妹妹無所事事。從小到大,她都是和姐姐、妹妹同住一個房間,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的獨立空間。有時候她寧願去上晚班,這樣白天就可以一個人在家睡家了。家裡房子很老,每年一到冬天,父親就用厚塑料布把窗戶封起來,但冷空氣還是會鑽進來。無論地暖開多大,房間都不暖和,凍得人直打哆嗦。
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桂娜強烈的危機意識,使她年紀輕輕就開始操心養老問題。她一度計劃50歲以後退休,去濟州島度過餘生,用一輩子的積蓄買一間舊公寓。理由是越晚退休越費錢,人上了年紀后,身體各部分都開始出現問題,要去醫院看病。「反正我已經想好了,最後肯定選擇自殺。我可不敢想象,自己一直活到90歲、100歲,到時候顫顫巍巍的,站都站不穩。」桂娜說。

從小到大身邊許多人的經歷,桂娜看在眼裡,越發不敢對生活抱有希望。小時候,阿峴市場很熱鬧,人們都說只要去那做幾年生意,都會變成有錢人。可是桂娜發現,這麼多年過去了,市場里賣甜甜圈的奶奶並沒有變有錢。於是她想,韓國雖然成了發達國家,首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「可有些地方、有些人,依然和原來一樣,沒有一點改善。我就這樣待在這裡,沒人能保證我的明天會比今天更好。」
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,桂娜漸漸意識到,自己的痛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,而是被一種牢不可破的系統支配著。很多年裡,她一直過得渾渾噩噩,直到聽到一首歌。那首歌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,由韓國歌手Turtle Man演唱的《Bingo》,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。歌詞其實充滿正能量:「我熱愛腳下的土地,從未想過移民。」但桂娜卻聽得有些生氣,「每個人都覺得活在這個國家很累,心裡暗暗盤算著移民,可是又不想承認,於是用這首歌來催眠自己。」可是話說回來,為什麼不可以移民呢?那一瞬間,桂娜腦子裡冒出這個念頭。很快,她決定不去濟州島了,而是移民去澳大利亞。

《我討厭韓國》的故事沒有太多跌宕起伏,小說情節完全談不上引人入勝。主人公出國前後的生活都平淡如水,無非是描述移民念頭的產生和執行,寫成新聞特稿都不夠特別。但正是這種「普通」讓她看起來異常真實,無論是她的困境,還是她的掙扎,都像極了一個生活中的普通人,沒有大起大落的驚心動魄,有的只是小刀割肉的悲涼與刺痛,很符合生活流作品的特點。
近年來,韓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,在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作品中有所體現。電影《寄生蟲》對韓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揭示掀起了廣泛的探討;《我的解放日誌》對城市打工族的疲憊進行了細膩呈現;韓劇《天空之城》對中產家庭的教育焦慮也有深入展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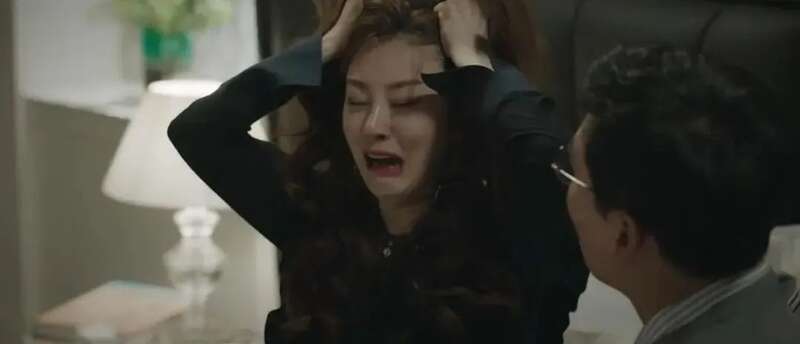
《天空之城》劇照
韓國文藝作品的敏感與其社會環境的高壓密不可分。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最新調查,2022年韓國資產上游20%家庭和下游20%家庭之間的差距創歷史新高,第一檔家庭的平均資產為16.5457億韓元(873.3萬元),相當於第五檔家庭平均資產2584萬韓元(13.6萬元)的64倍。殘酷社會競爭導致的教育內卷,在韓國也貫徹地相當徹底,學生能否考入SKY大學(首爾大學、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),直接決定了他們的未來,而這部分人只有2%。嚴峻的社會壓力直接反映到了生育率上,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《2022年世界人口狀況》顯示,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三年全球墊底,2022年這一數據為0.78。
結合這些社會現實去看《我討厭韓國》,會令人忘記它是本小說,其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內心的真實呈現,足以跨越情節和文筆勾起讀者的共鳴。作者經常會通過一些並不重要的情節來闡釋對事物的看法,對抒發觀點的重視甚至超過了塑造人物,可見其書寫動機多大程度上是由對議題的關注推動的。

在書中,作者經常借人物之口來諷刺韓國人。桂娜在澳洲交往的男友瑞奇是印度尼西亞人,他曾經在桂娜面前數落韓國留學生:「對韓國人來說,最上等的是澳洲人和西方人,之後是日本人和韓國人,再之後是中國人,最後是南亞人。可是在澳洲人和西方人眼裡,咱們全是東方人,他們根本分不清哪個國家是哪個國家。」當然,對韓國最狠的批判,還得交給「犀利姐」桂娜:「我的祖國只愛她自己,愛大韓民國本身,所以她只愛惜那些為她爭光的國民。比如金妍兒,比如三星電子。」
可以想象,改編成電影后,這本書里有多少觀點可以作為「金句」流傳,作為觀眾的「嘴替」讓人過把癮。不得不說,這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題材走捷徑的方式。比如作者在書中將幸福劃分為兩種,「資產式幸福」和「現金流式幸福」。前者是指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,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心裡,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供人支取,勤勞工作和攢錢買房就屬於此類。後者是指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,所以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的幸福,靠每個瞬間活著,桂娜想要的幸福便是此類。
對整個故事來說,桂娜出國后的生活到底有沒有變好?恐怕是讀者最關心的問題。小說通過一系列細節堆疊起桂娜的變化,其中許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感。

《寄生蟲》劇照
到了澳洲,桂娜報了一所語言學校學英語,為拿綠卡做準備,同時在餐廳打工。漂泊在異鄉的日子當然不容易,她租的房子由車庫改造而成,15平米大小,裡面只有書桌和床。因為英文很差,她只能做廚房雜工,連最低時薪都沒達到,只能拿8美元。但她依然一點點喜歡上了澳洲,也在對比中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更清晰的認知。澳洲地廣人稀,道路寬闊,陽光燦爛,與首爾的陰冷、擁擠截然不同。走在悉尼的街頭,亂穿馬路差點被車撞死,司機沒有罵她,而是一個勁兒地問她「還好嗎?」人們都很平和。她在澳洲結識的朋友,都活得瀟洒不羈,人生主要的任務是吃喝玩樂,而她在韓國的閨蜜們,則在十年如一日地抱怨工作和婆婆。
更重要的是,桂娜開始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自由的選擇。在澳洲,白領和藍領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不相上下,沒人爭著去坐辦公室,反倒認為干體力活也不錯。桂娜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同胞載仁便是如此,他一開始是為了學會計,後來發現對會計不感興趣,便改學了廚師。做廚師不需要碩士文憑,只需要在烹飪學校接受不少於900個小時的培訓,再實習一年,就有資格申請綠卡了。
當然,澳洲綠卡也有許多務實的好處,桂娜對此如數家珍。有了綠卡,就算不工作,也可以按月領失業保險金;得了大病,國家負責全部醫藥費;第一次買房,可以拿到2萬澳元左右的補貼;大學生子女每年能得到幾萬澳元的學費補助。

而另一方面,桂娜對韓國的恐懼並未消失,甚至進一步強化了。來到澳大利亞幾年後,桂娜聽到《Bingo》原唱歌手Turtle Man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。死之前他的生活已經很窘困,因為經營公司不善而債台高築,無錢支付高昂的醫藥費。與此同時,桂娜以前工作的金融公司也暴雷了,信用卡部門取消,一位員工自殺。桂娜想:「如果我依然留在韓國,能否抗拒這個命運的齒輪?恐怕不能。」
拿到澳大利亞綠卡后,桂娜曾經因為感情考慮回到韓國,最終還是放棄了。那次嘗試,讓她意識到,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與前男友志明短暫複合期間,桂娜回到韓國與他同居,同時嘗試找過工作,但找了幾輪都顆粒無收。想將注意力轉移到生活,也同樣無望。桂娜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貴,而是可以買到便宜的食材和酒水,住在溫暖有陽光的地方,身邊的人都愛笑,每月都能看看話劇、約約會。但這些男友都無法給她,他在電視台做記者,每天下班回到家已經是凌晨,經常忙到沒有休息日。一次,桂娜問志明:「你難道一輩子都要加夜班嗎?」志明回答:「所有人都這麼活著。」桂娜反駁道:「澳大利亞可不這樣。」於是,她決定第二次跟志明分手。

分手后,桂娜徹底決定待在澳洲,爭取拿到國籍。這次她的決心更堅定了,因為積極的念頭比消極的念頭有更強大的力量:「我這次去澳大利亞,不是因為討厭韓國,而是因為要變得更幸福。」
現實中,許多韓國人和桂娜一樣,選擇通過移民來改變命運。2016年,韓國媒體公布的一項移民調查顯示,78.6%的受訪者有移民傾向,移民理由靠前的幾位是:工作環境惡劣;收入不平等問題嚴重;對退休生活的不安。另一方面,許多年輕人正在逃離以首爾為主的大城市,選擇返鄉務農,韓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,2020年以來,有近50萬韓國人遷移到農場和農村地區,同比增長7%,其中二三十歲的青年佔一半。
種種人口流動跡象都表明,韓國人已對故土失去希望。現實主義作品的流行,不過是呼應當下人們最關心的話題。